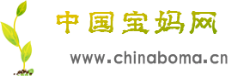但是周姨却常常被那里的女主人请进去,因为她弹得一手好琴。
一曲梅花三弄,常常透窗而来,为我的童年的生活注上精美的音符。
为了让小车能一直开进后花园,座落在中轴线上的大厅被拆成了通道。
以前大厅两侧的回廊就废弃了,一个以收荒为生的爷爷把他租了下来。
他头发花白,面容清癯,腰背却总是挺得很直,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气。他先用断砖堵死回廊,再把大厅的屋椽接过院墙,然后砌了一个灶台一方石桌一张床。桌面是一方不知道从那里搬来的红沙石,他用钢钻在上面打出一个棋盘。十九道横线和十九道竖线交叉起来,庄严无比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围棋,黑白子很神秘也很可爱。荒爷爷过世那个晚上,就是在独自摆弄一个难解的棋局,人落了气,身子还斜靠在墙上,一只手还抓着一把棋子!
围棋着星宿,演绎着万物的成理。
棋盘的中心天元,意味着最初的统一。
一天,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进院来,打听一个叫徐炳文的人。
大家都告诉他说院里没有这样一个人,他就是不信也不走,极力描述着那人十几年前留给他的印象。还是周姨想到了收荒的那个爷爷,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,大人们也都跟着小孩叫他:荒爷爷!
搭上话后,竟越说越象,周姨就把那人让进了自己客厅。
“他搬来也不久,一个人总不和我们多说一句,生活上也没有个照应,你们做晚辈的也忍心!”面对责难,那人低下头,脸色有些微微发红。周姨让了坐,沏了茶,应酬周倒而得体。“童年失亲,老年无子,不管怎么说都让人看着难受……你是他的什么人?”
“棋友!我这次专程从上海来找他,只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遗愿。二十年前,他和我的父亲在棋枰上相识,订下了一年手淡一局的誓约,我这是代父亲如约前来……”
“哎……”不知道为什么周姨发出一声长叹,使得她的女儿不自然地扫了她一眼。就在周姐准备牵我出去玩的时候,荒爷爷大步流星地赶了回来。
棋局在大家的张罗下,就在周姨门外的小天井里摆开了。
最初寥寥的几严子,竟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摆上去。“叭!”棋子叩在石面上清脆而有力,接着就是无声无息的长考,仿佛他们正在进行的并不是一局棋,而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斗。
所有的思想,所有的力量,所有的手段,都是通过一严严棋子来表达的。
天色暗了下来,围观者牵来灯,周姨不失时机地递上了两碗蛋煎面。我想没有人能看懂他们的棋,但人们还是饶有兴趣地看着,没有一点声音。孩子们没了大人的招呼,就在院子里疯跑,我总是注意着等待着下一严子的叩击,常常是我跑累了,那严子还没有叩下去。
没有人知道那局棋是好久结束的,也没有知道那局棋的胜负到底如何……
第二天清晨,桌面上白子收成一堆,黑子收成一堆,而来人已走,荒爷爷也挑着担子收荒去了。
第三章:文革
我能记住的第一个历史事件是文革的武斗和游街。
振奋的红卫兵以及惶恐不安的男女老少,从我的眼前晃过,就象过皮影戏一样。有一天,院里的杨弟拉来一群红卫兵,围住一儿两女的陈家。说是陈家的大儿子欺负了杨弟的小妹,就那个走路一颠一颠的陈家老大吗?怎么可能欺负要强的杨妹,大人们只是摇头……
院里堆满了人,没有人敢出头去招惹他们。门被撞烂了,陈家的两个小妹被拖了出来,一群人手执军用皮带,指着她们的身上就一阵乱抽……这时她们的父亲冲了出来,举起一根扁担,扫倒一片。
杨弟掏出了一把火药枪,指着她们的父亲吼道:“给我跪下!”父亲没有屈服,着将上衣一把撕开:“来呀,小子,有种就开枪!”
“一个国民党的兵痞子,现在倒神气起来了!给我打,朝死里打,看他还敢不敢嚣张!”杨弟红着眼扣动着板机。四周没人敢出头,只是把自家的小孩拉到身边,闭上眼……
枪很久没响,只听到他们的嘈杂声,他们开始用通条通枪,原来那枪哑火了。更没想到的是,这时枪竟响了,倒下一片,通枪的那个人满脸都是铁砂子,血肉模糊!
而庄严的陈家父亲还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,虽然身上有几处血迹。
这是勇气的力量?还是正义的力量?
那时,大人们象不用上班。
前院的小天井里,天天有两个人下象棋,从早坐到晚。一碗茶喝了又喝,完全成了白开水,还是慢慢地呷,象有无穷无尽的韵味似的。每每在我还看不出谁胜谁负时,他们就推子认负了,双方都面带微笑,只是用手指划着棋盘……我就好奇地问:“你们谁胜了?”
他们都用手指着对方,相视而笑!
他们一个就是荒爷爷,而另一个叫许爷爷。
他们都很喜欢我,常常用手抚摸着我的头,边下棋边给我讲故事。精卫填海、夸父逐日,最初就是他们讲给我听的。
荒爷爷每天一大早都出去撕大字报,天刚刚亮就得回来,被人看到了那可不一定还能走着回来!那怕就个把小时,找到一天的饭钱没有问题。
荒爷爷的生活十分简朴,常常是几片泡青菜就下一碗饭。但是他的泡菜却出奇地好吃……那滋味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。
陈家出事那天,荒爷爷恰恰不在,说是收一个古玩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