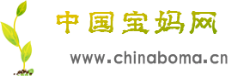十多年后,经常有人在这里久久徘徊不去。他们有来自台湾的老兵,有已经风烛残年的母亲,有为了撰写共和国史的资深学者,有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。
他们只好捧起黄土,默默地带了回去。
那天,接待我和父亲正好是我的接生医生和护士,父亲要我叫他们刘伯和陈姨。那天,我住宿的窗外就是那片南瓜山。不知道为什么,总是睡不着。我呆呆地看着在那里纷飞的莹火虫,其实很可能是磷火。
大渡河的滔声远远传来,如哭如诉……
第二天,我醒来时,下夜班的陈姨给我带来了稀饭和馒头。
“打针了!”外面有人在喊,接着就是一阵笑骂。原来我住的是护士值班室。“你的爸爸外出架线去了,下午才能带你上山。”
“架线?”我拿起馒头不解地问。
“对呀!你的父亲克服了很多困难,为我们建起了水电站,现在需要架设电线把电送往各队。”
陈姨不到四十岁,给人的感觉很亲切。
“等吃完了,陈姨带你看看这里的大山大水。成都城里没有山,公园里的那些土堆哪里能称为山呵!”
“陈姨到过成都?”她没有回答我,却转身推开了玻窗。外面的晨雾还没有散尽,远远的一树红叶在山顶上就象一支高举的火炬。
“生如春花之绚丽,死若秋叶之静美!”陈姨随口说了一句无法理解的话。
南瓜山的得名,据陈姨说还不是因为这里种着南瓜,而是出于他的外形。
“你来看,它象不象挂在天际落地而生的巨瓜?圆圆的外缘把大渡河挤出了一道的弯,河对面的北山就象守瓜人的小棚。你再看,它山上的石岗高耸入云,细细的就像挂在天外的瓜茎。”
那天上午,陈姨带我爬上了石岗。上面松柏苍苍,掩护着三座用青石砌起来的炮塔。它北控亘堡,南望连绵不断的凉山。一道河水从南面流来,绕过石岗向西汇进大渡河。它的东面,就是我和父亲昨天翻过的那个山梁。
陈姨还告诉我,沿着南面的小河,一直可以走进农场。
当地人称它为枯河,其实它的水量十分充沛,枯河应该是哭河的误读。上面有座很古老的石桥,陈姨来的时候就叫哭桥,现在也被写成枯桥了。
现在父亲的电站就在枯桥的下面,而母亲却在更里面新垦的茶山上。
当天晚上父亲带我来到他的发电房。
那是一个夹在两个巨石中的小楼。就象一块不小心掉在那里的积木,因为实在不好拣,就没有人管它了。木楼的顶上就是枯桥,有一道小渠穿过石桥的阐门直冲小楼而去。
小楼分两层,下面安装着发电机,人住在楼上。推开房门,里面一个三岁大的小孩,正伏在地上推着半截砖块。“这就是你的弟弟。”爸爸刚说完,那个小孩就爬了起来,向门口钻去。
“喊你的哥哥,你不是天天闹着要喊哥哥吗?”爸爸一把抓住他,弟弟急忙说:“我要尿尿!”
父亲放了手,他就在门外对着山叉开了脚。半天没有动静,他又跑到房外的岩边上蹲了下来,一只手秦乱地扯着野草。
小屋不大,但被一个人在家的弟弟翻得很乱。爸爸收拾起来,很快就用木箱为我拼凑出了一张小床。我坐了上去,满意极了。因为我除了和婆婆爷爷同过床外,还没有和别的人睡过。我给父亲说了,我不睡都可以,绝不和弟弟一起睡!
弟弟回来了,看到新床也高兴得又是蹦又是跳的,最后他干脆爬上了床。我看到他的脏鞋子在爷爷给我的新床单上边踩边蹬,真是气极了,一掌就把他掀了下去!爸爸抱起弟弟,没有说我也没有打我,我也没有看出他的心寒!
我进山的第一夜,就是在弟弟没完没了的哭声中度过的。
第七章:农场
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的北缘,一条八十公里长的机耕道绕着它,最后伸进了林海。沿着弯弯曲曲的机耕道,布置着十多个劳教中队,队与队相距很远……因为以前这里有近万人,灾荒年以后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。
恐怖的饥饿和死亡,就像根本驱不散的乌云,一直压在那里。没有人再去提它,但它却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浮动着翻滚着……从压抑的神色中,从长长的叹息里,从忧郁的对望间,我感到的是末日就要降临的气氛。
对我的出现,大家十分惊讶!
因为我的诞生近乎于奇迹,好象刚刚飘散的生命都汇集在了我的身上。我出生时不足五斤,母亲不仅没有奶水而且很难找到吃的,都没有想到七年后我能站在他们的跟前……
在山上那段艰难的岁月,他们很多人视我犹如自己的子女。
五六年,这里刚刚平息了一场彝族头人的叛乱。
硝烟还没散尽,一部分参加平叛的战士就划给了省劳改厅,奉命在这里开垦组建农场。农场的吕政委,当时是平叛部队的营长,于是这部分战士就成了农场管理的骨干。
五八年,最初到这里的劳改人员,不是释放就是转走了,这里改成了劳教农场。除了接纳当时各地划出来的右派外,还接手了原来由宋庆龄基金会管理的几个少管所。
那时的少管队就在枯桥附近,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莽莽苍苍的老林。
当时,这里由吕政委带队,我的父亲是少管队的文化教员,母亲和陈姨是卫生员兼保育员。
野兽出没,山洪暴发……一次,母亲起夜,一条蛇竟爬到了她的床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