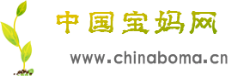几年以后,我寻着原路找到那里,但是却找不到了那个果棚。
听说一场大雪,早已把弱不禁风的木棚压塌了。大雪后的第三天,才有人想起了他,在果棚里刨出一具冻硬的遗体。
很久以后,我在梦中,再次聆听到了他饱经沧桑的声音。
是什么把万有收成一握,给它们注入最初的?又是什么给万有以命定的属性、腾飞的力量以及庄严的次序?当我们从万有的手中领到生命和智慧,有谁知道这些也会滋生贪欲与罪恶,从而引向毁灭。
说完老人陷入了沉思,良久又改口说道:流水不腐,生生不已自有自我洁净的能力!我们是否肩负着万有自我认识、自我完成和臻于至善的使命?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重建一个更人性的世界秩序?
凭着少不更事的童心,我天真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。
老人一下站了起来,激动得来回走动。就象疾风中的秋木,失去了光泽的叶片纷纷离枝而去。老人弯下了身来有些委琐,我那时还没有能力看出来,在衰老与压力中,老人的生命竟是那样挺拨有力!
老人挺直腰,手习惯地找着什么。
我想老人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最高学府的阶梯教室里了,老人环视着自己的莘莘学子和坐在后排听课的海外学者,骄傲地拾起粉笔,在黑板上挥臂疾书。
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!”
老人回过身来,教室里再次响起洪亮的声音。
这一直是我们先哲百折不挠的精神追求。五千年了,是他们不断擦拭也不断地磨励着我们民族的梦想。从三过家门而不入,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……千年一脉,生意盎然。
第九章:母亲
两个多月过去了,我还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。
元旦来了,弟弟一大早就爬了起来,说是要去采花。寒冬腊月风雪满山哪有什么花?但弟弟竟采回了一串串鲜红的浆果。他用一个大碗装满雪,让父亲把它们插到碗里去,说是要送给妈妈。
我不知道那浆果叫什么名字,只记得它们在雪碗里就象跳动的火。父亲说要到山下为母亲买面,我们就索性上床钻进温暖的被窝,等着妈妈的到来。渐渐地我和弟弟都坠入了梦乡。门再被父亲推开,已经是暮色苍茫了,碗里的雪早化成了水,浆果也都倒在了桌子上。
“妈妈呢?”父亲放下背上的挂面就问。看到我们一脸的茫然,他就没再说什么,只是捅开火,开始为我们下面。我还是听到了长长的一声叹息,我感到自己的心一阵颤栗。
这时于丽来了,穿得鲜艳动人,并递给我一张手画的贺年片。画面上只有一个小雪人和猫,憨态可掬。
父亲拿出爷爷给我准备的糖果。于丽好象很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糖纸,只见她一个劲地选,不停地吃,把弟弟的一双眼睛都看大了。但毕竟是于丽的欢歌笑语,给我们带来了仅有的一点新年气氛。
送走于丽,又到了父亲的学习时间。
父亲犹豫了半天还是走了回来。他问我:“你背过东西吗?”我摇了摇头。“你最多能拿好重?”我盘算起来,每到星期天,爷爷就会带我上街买一周我要的糖果,我争着拿过,它们一般有两三斤。但是我不敢说只拿过两三斤的东西,心一横就说了个八斤吧。刚说出口心里就后怕起来,心想我看你怎么拿得起来!
“好呀,这是七斤面,你给你的妈妈送过去!”
“我找不到路呀!”我一听就吓了一跳,我刚才看到父亲放它们下来时很沉,连忙想找到一个借口。“弟弟会给你带路的。”我试着去背一背,真沉呵!我第一次起身时,竟脚一软倒在了地上。
“慢慢站起来,你能背起来的!”父亲满怀深情地鼓励着我。我突然生出一种英雄气概,憋足气摇摇晃晃地背着它站了起来。“老沈,于队长叫你!”一个声音远远传来,爸爸顾不得多说,就跑了出去。
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就这样留给了我!
群山深处的隆冬是那样地幽清。割面的风无影无形。山路很陡,我的手不时伏着地面,完全是在爬。汗水浸透了内衣,一歇下来就凉。
我反复问弟弟还有好远?他总是说就在前面!山高月小,石路如蛇,我看不到弟弟所说的前面究竟在哪里。心越跳越急剧,给我一种濒死的感觉。有时仿佛人都飘了起来。有时又感到自己在不断地往地里陷,所有的一切都向我压来。
“我去叫妈妈!”弟弟看到我情形不对,撒腿就跑。我把背着的面靠在山壁上,喘着粗气。
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,月色一暗下去,雪就飘了起来。开始是一片一片地飞舞,后来就是一团团地往下砸!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弟弟才找来一个不是妈妈的女人,弟弟叫她瞎婆。
看到我满身是雪,只说了一句:“真作孽啊!”她背起面,我和弟弟跟着她一阵小跑,很快就到了藏在山凹里的女子中队。
她把妈妈从学习室里叫了出来。妈妈看了看我,问道:“爸爸买了多少面来?”我怯生生地回答:“七斤!”
“七斤怎么够?”妈妈的声音一下就高了起来。“我叫他买的是十五斤!”这时,背面的女人用一杆称吊起面来。“鬼说!整整十六斤多!这年头,就连自己的小孩都要骗!”
我听到这话,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,而且根本就收不住。我当时真的不想哭,只想一个人去死!
面对母亲站在川医大门前满头秀发的照片,我第一次对命运的鬼斧神工感到如此真实的恐惧。她斜依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旁,双眼充满了兴奋和希望。两旁还有几个扛着行李的新生,他们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了丰姿绰约的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