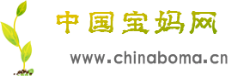我失语了,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忘记了说话!
当然失语的还有历史,还有早已沦落沉迷的良知!
第十七章:红崖
为了解决就业人员婚后住宿,农场终于在女子队修了宿舍。
父亲带着我搬到了母亲那里。我们一家人也终于有了自己共同的空间。
那是一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,仅有的一堵玻窗开得又小又高。父母的床尾横夹着我和弟弟的上下铺,留下来的空间放了一张桌子和两只小木凳后,仅能容两个人在室内打个转身。
柴灶打在室外,常常是饭菜一锅煮热后,一人添上一碗,靠着墙几口就扒完了。晚上烧热了水,一般会洗了脚才进屋来,室内实在狭窄得让人窒息。
到了周日,妈妈一早起来,就要把全家换下来的衣服端到河沟里去洗。我和弟弟则到山林边上拣拾枯枝,负责备好一周热饭烧水要用的柴禾。
队里其它人员,住在大寝室里。
十六个人一间,除了床仅留有一人能过的通道。
男队寝室静得难受,人和人之间基本没有交流。在女子队里却是吵得要命,指东骂西,摔盆打碗……由于劳动强度和思想压力都到了极限,很难再去控制情绪体谅他人。这是一个裸的世界,人们为着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挣扎着也倾扎着,最终都习惯了持强凌弱。
以前,女子队还有男干部,连续几起桃色事件后,就全部换了。
当然,管理也跟着加强了,最后一丝怜惜和迁就,也全都换成了呵叱。
队长姓刘,是一个北方人。
她四四方方的脸很象男子,人也显得很高大。
她给我的第一次印象,就是那次在全场蓝球赛上。看得出来,她的自尊心很强。当薛菲全力以赴地赢下比赛,我看到她开心地笑了,和场里领导开着玩笑。当时,她的确没想再捆薛菲……
是薛菲等着受捆的姿态激怒了她?翻脸一变竟凶狠十足!
她的孩子张涛,前不久才从外地转来。知道米娜老师的班带得最好,就插到了我们的班上。张涛年龄比我们都大,成绩却不好。由于很多时候,他的作业都需要由我完成,无意之间使我知道了一些队里的事。
整个女子一队都深陷在一个山坳里,最里边靠着一壁断崖。
沿着湿浸浸的崖缘,爬满了深红色的苔藓,有五米多高,都叫它为红崖。
队部紧靠红崖,俯瞰着全队。那里中间是队部办公室,左边通着会议室,右边一排是幼儿园、保管室和大食堂。队部前面有一个操场,早上晚上都要在那里集合点名。队部的里面是干部的小食堂和医务室,还有一间独立的砖房是队里的禁闭室。
那是一个套间,中间隔着铁门。里面的单间,一半深入了地下,又矮又窄,地面上总是集着水。
这应该就是关过薛姨的地方。
我实在无法把薛姨和这个环境联系起来。
那份青春,那份活力,在这里该是怎样地窒息和绝望!
瞎婆在医务室工作,行动相对自由一些。
瞎婆看起来并不老,她的烟隐很大,抽得极有风度。
不知道在农场的档案里,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但我知道她在华西医大读书的身分是假的,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务。瞎婆并不瞎,其实她双目不仅有神,而且具有魔力。叫她瞎婆,是因为她姓夏的缘故吧?瞎比夏顺口!
那时,她深受队长的信任,常常能看到队长坐在医务室里和她聊天。
由于,她还是后勤生产组的组长,队上总是把最不服管教的人员交给她。
最近,九妹从母亲所在的采茶三组调到后勤,其原因应该源于赵平叔叔。
九妹是一个孤儿,进场时还不到七岁。
总是嘟着小嘴张望着,好象什么都看不厌烦似的。常常缠着陈姨,不回去睡觉。一天夜里,一条蛇爬到了床边上,她竟想去捉它……
一天,父亲带我上山打柴,无意间说起了发生在少管队里的往事。
刚好,你的妈妈起夜回来,吓得不行。对蛇有办法的还是你的陈姨,不知道她是怎么把蛇引出去的。
山上蛇很多,开始大家也打,后来蛇群围攻了我们住所。
当时,都听到了嗖嗖的响动,以为是风。细细一想,才发现不对,那晚出奇地黑但没有风。有人点亮油灯,推开门想看个究竟,人一软就倒在了地上。成千的蛇游动着,蛇芯飘飘,蛇眼森森……
好在打翻的油灯,引燃了火。
可能,发现不该对我讲这些,父亲改了话题。
那时场里成立了一个文工团,就住在这里。每次排了新的节目,整个县城都象要赶到这里来,过一个快乐的节日。他们举着火把,沿着几十里山路,远远看去就象一条艳红的游龙。当时,全省不少杰出的艺术家都汇集到了这里,可惜的是很多人都没有熬过灾年……
前几年,为了庆祝九大闭幕,场里重新把他们召集了起来。旧的节目没法演了,就排了一场《红色娘子军》。十年磨难,以前几个从歌舞团送来的演员,再也跳不动了,只好让九妹和赵平从头学起。
正式演出那天,九妹扮演吴清华,赵平扮演家丁。出人意料的是,一开场赵平就用鞭子把九妹打得满臂是伤……
带着血痕九妹饱含地跳完了全场,赢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。
剧团追问过,不相信这是九妹的主意。现在回想起来,还真有可能。
父亲再次陷入了沉默,也许他深深地体会出了九妹内心中的苦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