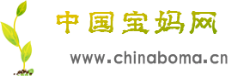但是,我还是被送走了。后来读了大学,才知道送我走,是因为我没有成都的户口,在成都上不了小学!婆婆爷爷当时为什么不给我说真话呢?这事我真的不能原谅他们。记得临走前爷爷还说:“你借钱给冲儿是没有错,但是说谎却大错而特错了,爷爷真的希望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!”
爷爷永远也不知道,他的这句话竟注定了我的一生必将坎坷不平!
通向火车站的大街,那时还没有其它行人。只有清洁工在扫着满地的梧桐树叶。整齐的路灯是那样地冷,拖在身后的阴影又是那么地长。
爷爷拿着行李,小声地和小姨交待着什么。小姨紧紧地牵着我的手,手心里竟沁出了汗水。她停了下来,抱起我并深情地吻了吻我冰冷的面颊。我还没满周岁,妈妈就把我送回了成都,多少年来小姨带我不少,但是我却一直不喜欢她。
到了火车站,四周开始热闹起来,热闹的其实只是小贩。真正的旅客都是那么地紧迫和匆忙。下乡的知青打着红旗,盲流的农民焦虑难安,小孩因为饥饿和口渴不停地哭着,母亲小心地剥着早已被挤扁压碎的熟鸡蛋……
爷爷把我们送上火车,方方面面都安顿好了,才下去。小姨没有说话,只是为我削苹果。爷爷站在站台上,又敲开我们的车窗,大声地说:“到了妈妈那里,就要听妈妈爸爸的话,过段时间爷爷就会下来看你。”
火车开始慢慢滑行,爷爷的身影越来越小,但是他的手还在挥动。每一次挥动都是那么地迟缓和沉重。
小姨的苹果还没削好,就滚到了地上。一群满脸是灰的流浪儿倒地便捡。列车员用脚踢他们也不知道。每人刚吃上一口,就被其它人的手抢了过去……
天亮了,广阔的田野上飘起淡蓝的晨雾。远远的是山,近一点的是竹丛,掩着一家家农户。一湾小河,一个小女孩在河边洗着刚采的青菜,她的手一扬,就激起一串水花。
火车钻进了大山,隧道一个比一个长。钻出隧道就是一道凌空的桥。一道小溪在沟底上流,细得就象线。陡立的山就象一个个巨人,刚毅而沉稳。
“准备下车了!”小姨轻轻唤了我一声。
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山间车站。站台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,而哪个是我的爸爸妈妈呢?
我兴奋地跳下火车,陌生的站台给了我坚实的一击。
“姐呢?”小姨冲着一个单薄的男子喊到。
他走了过来,递出一张火车票。“你姐请不到假,从昆明回成都的火车半个小时后就到。”小姨给他钱,父亲就象没看见似的,过来牵我的手。“这是你的爸爸!”小姨对我说,但我望着父亲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小姨上车时,塞了一张钱到我的手心里。“你去买本你喜欢看的书,小姨一直想送你的,总是记不到!”我知道这钱是她还给父亲的,就把钱给了父亲。
第六章:父亲
这里是凉山的北麓,我的父母在山上的一所劳教农场里,接受教育。
劳动教育的对象并不是犯罪人员而是人民,或者说是人民中思想有待提高的那部分人员。劳教农场下面设置了队,一个队又分成很多个组。一个队由管教干部担任队长、指导员、生产科长、总务科长和会计。组长是他们安排的人员,当然组长首先必须忠实地执行他们的管理意图。
在劳教农场里,劳动着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弃儿,他们有被家长送给政府管教的孩子,有取消妓院后,已经无家可归的女人,有国民党的残兵也有被抓获的匪卒,地富反坏右,三教九流应有尽有……本来劳动教育的最高年限是三年,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无论怎样自觉地接受改造,这些人一直没有受到社会的承认,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特定的身份,叫做就业人员。
我的父母就属于就业人员。
如果遣送你来的当地政府愿意接受你回去,就业人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人民中的一员,这叫住清放。但是很多人自己做不到这点,因为城镇的户籍管理很严格,除非大量地托关系找后门……我猜母亲那次和爷爷大吵大闹,就是为了自己清放的事。由于爷爷没有能力办成这事,所以母亲就一直在场就业。
只要还留在那里,只要还属于就业人员,就好象还没有改造好似的。不仅低人一等,而且从事着繁重得不近情理的劳动。
父亲牵着我的手,出了那个夹在大山之间的小站。
这里到处都是耸立的山,一条条淡黄的山道在大渡河的对岸,斜斜地向上攀沿望不到尽头。大渡河上用两根钢索拉起一座晃晃悠悠的桥,我鼓足勇气看着湍急的河水和一闪而逝的旋涡,突然感到一阵眩晕。
“会爬山吗?”父亲挑战似地问我!
小时候,我常常在公园的假山上玩,任由大人们在茶馆里剥着瓜子闲聊,于是勇敢地点了点头。但是我错了,这里的山真的太严酷了!翻过一坡又一坡,山势越来越陡,山道就象垂直的刀痕,令人感到恐怖。两边的荆棘划破了我的脸,山风一吹钻心的疼。我实在走不动了,就坐了下来,发现脚掌上竟生出了血泡,裤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挂破了。
父亲把我背了起来,矫健地攀登,敏捷的跳跃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父亲告诉我,他年青的时候,当过解放军战士。抗美援朝时,父亲所在的连队,就象电影里的王成那样,为了守住阵地,拼到只剩最后的七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