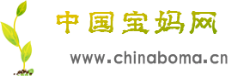妈妈走了过后,小姨对我更加冷淡了。
她总是说:“滚到你妈那里去,这里不是你的家,凭什么赖在这里?”
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住在深山里,那里的恶狗能咬倒身着军装的舅舅。那次舅舅因为腿伤在家里住了很久,他并不在乎腿上不断流脓的伤口,但总是心有余悸地说,幸亏没有遇到狼。
从此,我对父母那里,就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每次舅舅回来,他的那辆军用三轮摩托就停在门外。总有一群孩子在那里翻上爬下。更大一点的会挤进屋来,有话无话地找着舅舅问东问西,眼里流露出的全是羡慕的目光。
只有杨弟什么也不问,只是找我舅舅玩着军棋。虽然他屡战屡败,却没有人敢轻视他。一次,他发挥得十分出色,眼看舅舅就要输了,他也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没有想到,舅舅拿起一个地雷,做出一副就象是一个工兵要去飞的样子。这时,舅舅借着照看我为由放下棋没有动,象是忘了该走什么一样。
杨弟上当了,不加思索地用师长去碰了雷。胜负移手,杨弟当然不服,没有想到舅舅竟潇洒地说了一句:“兵者,诡道也!我这是给你开下眼界!”
杨弟红着脸收拾着棋,其实心里在发着狠。
我家住在大厅前的西厢房里,它中间有一个客厅,两边各带一个耳房。婆婆和爷爷各住一个耳房。我的婆婆长期患有胃病,成天都躺在床上。爷爷在市郊的银行营业所上班,早出晚归。
爷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,为我挤上牙膏温好早饭后才骑车上班。晚上八点过回来,起火做饭常常要忙到深夜十一点以后。因为不会炒菜,他天天都做白糖稀饭,而且常常熬糊……星期天就带我到饭馆里去吃一顿好的。
婆婆自己开火,胃痛起来就炕一锅炒面,一吃就是好几天。这时,我的午饭就只好东家问西家要了。菜当然不好再找人要了,于是是切点葱花拌酱油,也别有风味。从小就是这么过来的,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不正常。
我的婆婆和爷爷在生活上不仅没有照应,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你的我的分得很清楚,常常搞得我不知道该到那边去吃饭。婆婆给我说了很多爷爷的不是,与此相反爷爷从来不向我提及婆婆,就象根本没有这个人似的。
他们孤独地过着自己比死还难受的生活,唯一的指望好象就是要把我带大成人似的。
我家的亲戚真多,各种称呼和排行总是记不住。
他们每次一来总是支使我去买东买西,我好不容易买了回来,新的事又接二连三地安排了过来。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要我去带比我还小的叔叔,因为他的辈份比我高,常常蛮不讲理。
他们和我的婆婆一样都姓丁,每次来都是没完没了地搓着麻将。
听婆婆说,她们祖上世居江苏丹阳。咸丰十年,太平军围城数日,丁氏宗族血战不支,所有男丁不是被害,就是投河殉国。
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
一把大火烧了丁府,一门忠烈录进了方志……
婆婆的曾祖当时在四川任知县,后升任松潘直隶厅同知。方志有记:“才识卓越,行谊清介,秉公爱民。”谁想到他最后竟被人安了个通匪的罪名,含冤而死。临终前,他只是对自己的孩子说:“不做官,不求人。”
现在,我知道清末的四川风云变幻,满清王朝的垂死挣扎凶恶无比。没有想到这早已翻过的历史一页,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深深地打下了烙印。
婆婆给我说得最多还是她的身世。
婆婆的爸爸幼年丧父,早早地担起了全家生计的重负。
不满十三岁,他便到一家当铺做了学徒。几十年下来他不仅把自己弟弟带大成人,而且两兄弟在四川金融界有了十分雄厚的家业。
当时的四川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……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家业该有多难。仗义疏财的性格,悬壶济世的追求,终于使家道中落。每次婆婆带我去看祖祖,他都在家中为邻里免费治病,稍有空隙便拿起一本线装书翻阅起来。
但是婆婆和他们关系却是怪怪的。
婆婆的母亲过早地撒手而去,后娘因宠而骄,对我的婆婆竟刻薄无比。那时的男人是不管家事的,婆婆天资聪颖却读不成书,心有所爱却被迫和后娘的侄儿结婚……婆婆总是一提起往事就默默地掉泪,我从来就不敢多问。
后来,婆婆那些亲戚一来,留下婆婆一个人为他们忙吃的,我就来气。都说我不懂礼貌,我不知道违心的礼貌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。
看到我的婆婆病倒在床上,经常找我过去吃饭的是住在对门的周姨。
那是院子里的东厢房,也是一共三间。孀居的周姨一人住一间,她的女儿周姐单独住在另一间耳房里。中间的客厅里放着一张很大的红木餐桌,所有的菜都是一小碟一小碟地端上来,七八样时令小吃总是让我口馋不已。
方桌靠墙的一方立着一个很大的彩陶花瓶,里面的鲜花四季不断。
入冬,换上了梅枝,那花是嫩绿色的,薄得就象玻璃。我看得有些发呆,引得周姨笑了出来。“这是绿梅,我更爱把她叫住碧梅,全成都就数我们后花园的品种最好。”
又是那个后花园,那里简直是我们童年生活的禁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