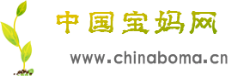我扯谎的真实动机,是给母亲出个难题!
我总认为我说的谎话完全可能就是事实!
如果成立,那么她惩罚我的理由就很不充分。其实母亲真的打错我的时候,也多次发生,我又能怎样?但是我喜欢让她感到有可能是打错了,于是总是爱为自己的失误寻找借口。
现在想来,这是一种依恋情结,总以为受了委屈理应可以换来一点关怀。
其实,母亲很可能最看不惯我的倔强。她不能也不愿说这不对,却明知道这不能见容于生活。也许,母亲需要找到一种情感的发泄途径,就像我曾多次用小刀自己划破手臂那样。
自己让自己疼,反常而又正常,因为我们可以用痛苦来确认真实,来确认自己起码还拥有这样的权力!
爷爷来了,爷爷终于来看我来了。
爷爷没有写信给我们说,他下了火车先到了医院,找到了陈姨。他详尽地询问了我和母亲的情况,因为我向他写的信与母亲告诉他的情况完全不符。
陈姨请了假,把爷爷送上了山就下去了。
感谢爷爷下了还我一个公平的决心。通过这事,我确认了自己在爷爷心中的地位。他疼爱的就是我,绝不是因为爱着母亲才对我百般迁就的。
不错,以前他也很爱我的母亲,现在母亲已经伤透了他的心。
晚上妈妈下了学习回来,爷爷的脸色立即变得严峻起来。
“你给我说清楚,沈铎究竟有好大的错,你这样待他!谁教你跋扈?何况是对自己的孩子!”
母亲面对着爷爷一连串的责问,不知所措……
爷爷是真生气了,我从来没有见到他生这么大的气。爷爷不是不想带我走,他说回了成都就为我联系学校,一有结果就回到山上来接我。但是爷爷不应该把自己留下来的钱,指定作为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,这样导致了整个家庭视我犹如路人……
那钱妈妈立即就甩给了我,家里的事也统统不要我做了。
准确地说,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再吃家里的饭,因为没人叫我吃,也没人叫我不吃。无疑,我已被家庭从心理上流放到了异地。
在整个女子队,我就认识三个人,她们是九妹、瞎婆和疯婆。
那天已经很夜深了,瞎婆看到我一个人站在门外,主动招呼了我:“你妈妈又打你了?看你冷成这样,瞎婆那里有火。”
她把我带到养猪房,用毛巾为我擦去了头上的雾水。
同寝室的只有九妹,队里还有一片只属于两人的天地?九妹为我冲了一碗奶粉,然后提开火炉上的水壶,拉着我坐在了她的身旁。
火燃得正旺,热力四射,把我的脸映得通红。
“妈妈不要我了,我想走……”想到伤心事,我的语音都变了。
“你能走到哪里去?这样吧,你到我们这里来,我去给你说!”
我摇着头,并不希望这样。九妹把我拉到她的怀里,低低地说:“瞎婆的话,你的妈妈会听的。”
果然,没多久,瞎婆就把我的东西取了回来。
第十九章:九妹
那间寝室就在养猪房的深处,对面是一间饲料房。
九妹跳过芭蕾舞,身材十分苗条,五官也很清秀。瞎婆比九妹还高一头,眉宇间既有女特务惯带的风情,也有军人的刚毅以及洞穿世事后的沉着。
她们安排我睡在饲料房里,弥漫的腐败和屎臭使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我固执地等着对门瞎婆和九妹熄灯,仿佛要等一切都陷入了黑暗过后,才会感到安全似的。昏暗的灯亮着,反而觉得到处都是飘动的阴影。
我听到低低的哭声,象是九妹的!
接着便是一阵使劲压抑住的和瞎婆的呵叱……
后来,好象还有一些细细地响动,被淹没在了一阵紧过一阵的山风中。
如果寻声而去,会看到什么?
没有敢去造次,但我脑子里涌满了幻像!
门开了,低沉的音乐响了起来。九妹赤着脚一闪而逝,紧追而来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。“生命何来?生命何为?为什么命运的皮鞭总是驱使着我们?”
他是谁?一身黑衣抖动着手中的长鞭,发出清脆的炸响。蓝幽幽的光,照在九妹皎洁的上。红痕累累,舞姿翩翩,只有一道道闪电就象追身的灯,关注着皮鞭下生命的挣扎和颤栗。
四周是那么地暗,音乐轰鸣就象魔鬼的愤怒。
突然,生命在绝望中奋起,主动地迎向皮鞭,让和皮鞭缠在一起。怒张的力把皮鞭绷得笔直,通过一只手传给另一个,就象亚当和夏娃传递着上帝制造生命时的秘密。
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,一切都伏向大地……
第二天瞎婆上班去了,九妹喂完了猪,开始为我做饭。
“张涛是你的同学吧?瞎婆已经托他为你请了病假。”
也好,我实在不想再去面对米娜老师的目光,我想自己下山远离这里。
“瞎婆是一个特务,她会害死你的!”
我鼓足勇气说出了想说的话,然后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东西。
“你要走?你能走到哪去?昨天,你的父亲找了我,知道你的母亲一时很难转弯,我才让瞎婆接你过来。”
“是你让瞎婆来找我的?”
“是呀!有什么不对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