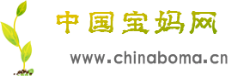后来,薛姨告诉我,场里以前有一个老人,用一生来研究我们的上古神话。老人坚信古人们不会把虚无飘渺的东西视为圭臬,每则神话都有其真实的起源,可以说神话就是那时一个民族的精神全书。
老人过世以后,他写的手稿就留在了老右爷爷这里。
时至今日,老右爷爷也已过世多年。我不知道这部手稿,是永远藏在了积雪的下面?还是以后又在人世间历经沧桑?
琥珀有泪,碧血有魂。多少精诚,多少心血,石沉大海。
“薛姨,你说一个人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什么?”
在回家的路上,我终于大胆地问出了自己心中的问题。其实,这个问题实在太大,就算我的孩子今天问我,我也很难回答。
“当然是诚实呀!你想如果没有了诚实,人人指鹿为马,混淆是非,颠倒黑白,那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基础!人和其它动物不同,离开了社会他将一无是处。人的生存需要一个以诚相待的集体,需要团结起来精诚合作去战胜困难。”
“那为什么诚实做起来这样难呢?”
“不难!难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勇气,也失去了做人的信心!”薛姨所说的人,显然是她心目中的人,问题是生活中的人们该怎么面对利益和原则的对立。薛姨毫不犹豫给出了自己的选择,并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!
生活中从来不会缺少楷模,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把什么树立成社会的楷模。
真理的光辉是明析的,它既勾勒出我们人性的庄严也照耀着其中的卑劣。
我再次见到薛姨是那年的十一国庆。
每年国庆场里都要举办一次篮球比赛。女子就两个队,但也要打一个第一名。我看到的当然不像是在打篮球,更象是打橄榄球,用掀用抱人围球转。女子一队出人意料地落了下风,队长的脸挂不住了,她用三轮摩托将还关在禁闭室里的薛姨接了出来。
她依旧用一张手绢系着头发,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。
刚给她松了绑,有人就脱了一件很大的运动衫给她,她把它松松跨跨地套在自己姣好的身体上进了场。接着比赛就成了她的表演,她就是被别人掀翻后,球还能出手还能进篮。
在赛场上,她是文明的,没有犯规的动作。女子比赛犯规基本不吹,也没法吹。无论别人怎么围攻她,她都一直带着一丝调皮的微笑。她玩命地跑玩命地跳,全身汗水淋漓。她展现着自己的青春、自己的球技也展现着自己身上一道道腥红的绳痕……
比赛结束,队长满意地看了她一眼,没有想到的是,她竟自己背过手来等着属于她的绳子。队长愣了一下,其实她可能已经打算这次就放了她。结果当然还是又把她捆了起来,大家不能理解的是最后收紧绳子时,竟用那么大的力。
直到她发出痛苦的,他们要的就是这个?
只有孤独才能发现孤独。
只有孤独才能洞视神奇和伟大。
由我缔造并由我统治的死亡之都,庞大得就象一个光荣的帝国。我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每一个人,寻找他们在那里的位置。那里的中心高高地立着一个塔,可以俯瞰全城。我在那里安排着每样东西的运动,规定着他们只能有的属性。
可是,我不敢邀请我的米娜老师进去。
我知道她的美丽和善良都不属于那里,她更属于于丽她们的笑语欢歌。她丰富的表情从来都是那么地出奇不意,却能在我的心里掀起温暖的涟漪。她的话从来都不是命令,却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认真执行。
她掌握着我不知道的世界,秩序井然但却充满生机。
春天不知不觉中走了过来,小草吐绿,枯木发芽。
五颜六色的鸟,跳着叫着,仿佛一定要我重新去思考她们。
学校的春季运动会都报名了,我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想参加。米老师找到我要我去跑接力,我不敢反对。我知道她看穿了我的心思,无论她安排我做什么,我都不会反对,但会以放弃的心态去应付了事。
一千米的接力赛开始了,我刚跑上道就觉得不对劲,果然没几步,破旧的布鞋就落了。“不要管它,跑你的!”身为班长的于丽,在赛道外拼命地向我叫喊,米娜老师也不断地向我挥动手中的小旗。我忍着巨痛终于跑完了全程,看着接棒的同学奋力率先冲过终点。
米娜老师在终点亲自帮我穿上鞋,深情地说了一句:“真的,你做到了!你为全班也为你自己赢来了荣誉。”
荣誉,一个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词。从老师的口中说出,就象她身体的某个部分,带着微笑一般的魔力。如果说荣誉是一个集体给以个体的肯定,那么我并不配,因为我并不想为这个集体付出自己的努力,我这样做了完全是因为我不愿让老师失望而已。
薛姨却不一样,她是那样地珍惜自己所在的集体。
进山时,爷爷给我准备了很多种零食。进山后,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吃它们,因为生活给我的痛楚绝非它们所能缓解。对我来说,只有回到了爷爷和婆婆的身边,才算逃出深渊。但是很快我的希望就化成了泡影。
一天,爸爸给我和弟弟发了几颗硬糖,我当即表示送给弟弟。爸爸没有同意,说了细水长流的道理,然后就把糖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。很多天过后,我又想起把糖送给弟弟,没有想到竟会找不到了。我认为是弟弟拿的,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