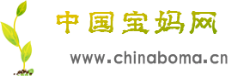问题是那时我根本就不认为我该来到这个世界上。
我没法选择我不来,但是我有权选择离开呀。虽然生命是那么美好,婷媛的勇敢,子夜的美丽,于丽的骄傲,还有米娜老师的善良,但这一切都是别人的。我既没有冲儿的强横,也没有于剑的刚毅,有的只是伤心和绝望。
陈姨的出现,毕竟给我的童年生活抹上了一丝暖色。
我发现那两个彝人就住在于丽的家里,那个老人象染上了重病。一天深夜,医务室的电话一阵惊响,陈姨和我都跳了起来。于队长让陈姨立即去他的家,我找到了电筒。我看到陈姨两手不空,就打着电筒跟了出去。
于丽的家有好几间,彝族老人住在最外面。他的女儿抓住他的手,看着陈姨消毒打针。老人想坐起来,于丽的爸爸过去帮他,不小心将痰盂踢翻了。于丽借机钻了出来,看到我又连忙退了回去,她的内衣很淡,十分好看。乱蓬蓬的头发带着迷人的体香。
彝族老人抓住于丽父亲的手,脸上泛出红光。他掏出一只玉璧,细细地看,直到泪水蒙上双眼。他的嘴唇起来,想说什么……眼里的光慢慢扩散。女儿抱着老人的双肩,没有哭没有呼喊,只是默默地送着老人离开人世。空气不再流动,时针轻轻一顿,这一刻叫人窒息。
女儿的手为他合上双眼,将玉璧捧在手上,双腿跪在了地上。我隐隐看到玉璧内有什么东西在运行,然后慢慢暗淡下来。于丽的父亲也跪了下来,接过玉璧,向天说着彝语,声音低沉而沙哑。
陈姨回过神来,悄悄地将我牵了出去。
我回头看到于丽屋里的那盏灯还亮着,想起她刚才给我做的鬼脸,还有那件米白色的内衣和淡淡的香气。
回屋后,我不能入睡。我听到陈姨低低的哭声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彝族老人散开的瞳孔就象一口枯井,我一不小心就滑了进去,疾速的坠落使我的心跳不断加快,湿腻的青苔就象盘踞的巨蛇。
我不敢开灯,我听到陈姨在轻轻地呼唤一个人的名字。
于丽很快就和陈姨有说有笑了。
她会主动地为陈姨择菜做饭,仿佛医务室就是她的家一样。
“死丫头,跑到这里就变勤快了!”
每次她的母亲来找她回去吃饭,都要给陈姨带点蔬菜瓜果。这些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,要多少有多少。陈姨收下后,有时也留于丽下来吃顿饭,和我一起做作业。
这段短暂的幸福时光,使我忘掉了心中的死亡王国。
陈姨曾经说过:“圆满是没有的,但是我们可以尽力而为。真理是存在的,但是我们只能不断地校正对它的认识。拯救我们的是爱,通过爱我们才能看到最神圣的光辉。”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
我又听到陈姨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。
那天夜里,雨越下越大,山溪里的水轰鸣不已。远远的闪电不时照亮整个夜空,蓝幽幽的就象来自地狱的光。“罗霄!你不要走呀!”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,使我和陈姨都惊醒过来。她拉亮灯,掀开布帘:“你醒了?”
对了,陈姨梦话里模糊不清的名字,就是罗霄。
“你怎么在打抖?”陈姨过来抱着我,她的给我带来了平静。她放下我正准备走,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:“陈姨,不要离开,我怕!”她用手抚摸着我的脸,把我的手放进她的嘴唇里,轻轻地。她就坐在我的床边,透窗而来的风翻开她的单衣,她也在瑟瑟。我把铺盖牵到她的身上,她也把双脚收了上来。
“罗霄是谁呢?”我没有深浅地刚问出口就后悔起来。陈姨仿佛没听见似的,半晌才不着边际地说:“有一个小姑娘,十分喜欢自己勇敢的表哥。”雨声连连,风好象停了下来。“表哥家很穷,没有办法就到姑娘的家里做工抵帐。姑娘高兴极了,天天跟着他上山放羊砍柴,调皮淘气。一天姑娘疯跑时掉下了山岩……”
陈姨完全陷入了既幸福又痛苦的回忆之中,而我竟不敢去看她,只好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雨。“两天后,我一醒过来就问管家,才知道他们把表哥吊起来毒打了一夜,第二天表哥就翻墙逃跑了。”陈姨靠在床头上,象睡着了,但泪水却不断地从面颊上往下落。枕头浸湿了,凉凉的,我不敢发出一点声响,只是紧紧地贴着陈姨,慢慢地也就睡着了。
解放时,政府在清理成都红灯区时,陈姨因为无家可归,先到了一所卫生学校,后来就进了农场。那天她讲的肯定是她的身世,故事的后半段她没讲,我也不敢再问了。
很多次回忆起那段日子,很多次黯然神伤。
为一个个善良而又不得不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。
他们都没有放弃生命,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坚持……
我不知道陈姨的心路历程,我想象过她年青时所遭遇过的巨变和痛不欲生的经历。在这个世界上,她已经没有了亲人,她不仅使我获得了新生,我相信她还给了很多人生活下去的勇气。
是陈姨把爱的概念植进了我的心田,虽然它的生长缓慢而又艰难,但是它牢牢地抓住了一颗支离破碎的心。它象阳光,澄清着我想不透看不穿的事物。
她屹立着,用自己生命的光,照亮那片苦海。
一天,我借陈姨出诊的机会,拉开布帘。
我小心地爬上她的床,躺了下来,呼吸着她留在那里的体味。我真希望我的生命和她有种更深刻的关系,轻轻地唤她一声:“妈妈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