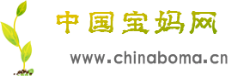父亲告诉我说,那时他们的营房和川医很近,每到周末他都能在学校的舞池里看到妈妈。不过那时,他只敢看看她,一次次在心里默默地祈祷,期待着某种不可预知的奇迹。
三年后这个奇迹终于出现了。
由于母亲的一位好友偷偷拿了同学的东西,学校调查时,母亲听信朋友的一面之词,作了伪证。当案情水落石出时,校方轻率地以同案犯为由开除了母亲的学籍。
由于母亲和她的那个朋友过于出众,几年来一直是流言蜚语的中心。也许是出于某种报复的动机吧?那位朋友才偷了一个高干子弟的手表。实际上她并不缺钱也不差表。
父亲从朝鲜回来,一直一帆风顺。母亲出事后不久,他也被划成了右派。当他脱下上尉军装,穿上不是囚衣的囚衣,竟发现了同样穿着囚衣的母亲。
这时,爱情以绝望后的果敢,在绝望的环境中绝望地燃烧了起来……历经种种风波,包括一个管教干部为之犯下错误自杀身亡,母亲和父亲终于走进了新婚的礼堂。
那一夜,父亲说他的心竟独自地对着所谓的命运发呆!
关于我的母亲和那个自杀干部的风波,可以说是建场初期曾被人人谈论过的话题。
我是在工作过后,才从我的一个同学那里听到的。当时我半天找不到一句话说,两眼根本不敢去正视那个同学。他并不是故意要使我难堪,所以好象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,只是顺着自己的话继续往下说……
你母亲那时一定很出众,一般说来那时的干部素质是好的,政治上坚定,生活上朴素。那个干部死后留下一本厚厚的日记,清楚地也如实地记载着整个事件的经过。当时几乎所有的人,都认为是你的母亲在有意地利用他,后来又翻脸检举了那个干部。好在这本日记,虽然没有公开,但总算证明了你母亲的清白。
在整个事件中,你母亲的勇气和决心都让人钦佩。
这事我至今没敢去问我的母亲,一次我小心冀冀地向自己的父亲提起过,他说他知道也就是大家谣传的那些。他不想追问事件的整个过程,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细说过……但那个事件肯定在母亲的心上留下了长期不散的阴霾,它毁坏了母亲的心灵和性格。
那事以后,女子中队里这类桃色传闻又不时传起。
主管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,除了那个自杀者外,又有好几个优秀的干警痛失立场。严厉,准确地说是严酷的管理制度出台了,劳动强度也加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,每天的政治学习都象文革的批斗会。
我看到母亲的那个晚上,会场前方就立着一个双手反绑的女子,散乱的头发盖住了脸,但从抽动的肩头上,我看到了她的哭泣。小指粗的麻绳陷得很深,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鲜红的血痕。
这不是薛菲阿姨吗?
瞎婆把面背走了,母亲急迫地向我说:“你等我一下,学习完了我给你的父亲写封回信。”母亲的身上满是泥水,眼里全是焦急,头发没有一点光泽。
“三组,三组的组长呢?”一个女干部大声地问。
“在!”母亲猫着腰,刚钻进学习室就站了起来。
“我们组开展了讨论,认为薛枫的错误有下面几条。一是平时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,表现在生活中倒菜倒饭,表现在劳动中拈轻怕重。今天出钱请山民帮她砍竹,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”
母亲好象一时找不到话说,最后好不容易才接着说道:“二是,从不承认错误,竟和批评她的干部狡辩,更是错上加错。说穿了这是不接受劳动改造。”
不知道为什么,我完全不能接受母亲的说法。我看着被捆的薛姨,头发上还夹几片枯黄的竹叶,脸上还带着枯枝平行划伤的血痕。
我觉得母亲的话是违心的,为什么要说违心的谎话呢?
会议散了,母亲和其它几个人,又被另一个干部带到室外,不知道是在安排工作,还是在查问什么事情。没多久,大雪就落满了她们的全身,就象一个个没有生命的雪人。
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母亲的。
我就是在那个晚上蜕去了童年的所有幼稚和天真。
妈妈和母亲这两个词,在我的心灵里从此失去了任何内涵,就象一对死后没有闭上的眼睛,空洞而漠然。多少年了,它就象埋进我里的弹片,又象膏肓里的沉疴,更象逼着多少天才自杀的隐疾。
我准备高考那年,父亲原先所在的部队派人来找到我们。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和标准的军礼,并没有给父亲带来多大的喜悦。而川医一纸关于改正母亲错案的通知,竟让父亲的双手不住地。
二十年的灾难岁月,二十年的艰难人生。多少次畏缩,多少次坚挺,多少次屈辱,多少次强忍……轻轻地就象夹在父亲手指间的纸,不停地跳动。
鲜活的生命偷走了,换来一张薄纸。
生命的尊严践踏了,留下一串文字。
苍天应该可以作证!青山也能作证!
终于,父亲用它包起母亲的一绺青丝,默默地夹进书里。
今天,当我拿起笔用心记载那段岁月,我发现自己的语言实在太贫乏,真实的生活和情感,都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。
我的父母无疑都是五八年那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