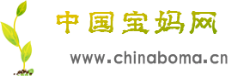没想到我的看法立即遭到了否定,因为弟弟从来没有这个习惯。
我又想要不就是老鼠吃了,父亲说老鼠从不吃糖,我没有这个经验,不敢反驳。我万万没有想到,父亲会反过来认为是我拿的。他的理由很简单,因为我有偷拿东西然后说谎的习惯。拿爷爷的钱是我错了,但这次不是。我说糖本来就是我的,吃了也是应该的,谁会自己无事找事?他说正因为这样,你怪弟弟拿了,我们才不得不补给你。
也许,我此时不再和自己的父亲去争辨是非,这事也就过去了。但我显然犯了薛姨同样的错误,为了诚实甚至不能默许某种错误的存在。
父亲说可以把队里的狼狗找来,谁吃了它就会咬死谁。我心里认定是弟弟拿了的,不敢答应是怕它真的一口咬死了弟弟。结果犹豫的神情,竟坚定了父亲的想法。到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,我同意去请狼狗也无济于事了。
这时妈妈回来了,她边骂父亲没有本事边找出竹杆。这是妈妈第一次狠狠打我,她一定要我承认做错了事。这是一次漫长、痛苦而又绝望之极的抗争,我无错可认,而且爷爷也不会同意我再做错事。打吧,打死我更好……我这样想着,看着自己的生命与外在的力进行撞击。
我现在都不明白,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坚信自己的观点。这事无疑使他们对我,同时也使我对他们都伤透了心。
在我的印象中,母亲很少有笑,说话又急又快,随时都会生气冒火。虽然,她经常打我,但我怕她更多的是出于心里的难受。
至到现在依旧如此。
第十一章:生活
那段时间,妈妈就在发电房的附近采茶,一天的定额是两百斤。
采茶是取芽尖和下面的一两匹嫩叶,如果要不伤到茶形,一天一个人最多就能采到二三十斤。春茶出来时,不立即下树就会老,而采茶的人手只有女子队。妈妈每天不到五点就要出工,到晚上十点都不一定能完成自己的定额。
一天,她到父亲这里找水喝,浑身都被汗水浸透完了。手指上缠的胶布一条条地散开,手上到处都是裂口,雪白色的皮肤一撕就落。父亲发现水瓶里刚好没水,就叫我抓紧时间去打水来烧。我知道妈妈的时间紧,结果忙中出错,把引水来的竹槽撞翻了,一些青苔流进了壶里。
如果倒掉重接,首先要重搭竹槽,估计要半个多小时,显然情形不允许。不取水回去好象也不行,妈妈说话的嗓子都哑了。我想水是从生满青苔的竹槽上流下来的,应该说青苔也是干净的,接的水也可以吃。
“死到哪里去了,接水要多久?”我知道妈妈已经生气了,离她勃然大怒不会太远。我哪里还敢多想,提着水就跑了进去。
大电炉很快就把水开了,妈妈倒出水来,看到水里竟飘满了绿丝,非常生气,就差把一盅开水泼到我的脸上。妈妈把水端到我的面前:“沈铎,你是不是认为这水可以吃?”妈妈立即恢复了冷静,好象是要和我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似的。
“是的,我想过一下……”没等我把自己的想法全说出来,妈妈就打断了我的话:“不用说了,你认为能喝的话,就喝给我看。”
“我可以喝的,但是水太烫而且我也不渴。”我坚信可以喝,但是被这样逼着喝毕竟很难受。爸爸过来了,也很生气,提起壶准备再去接水。
“不用了,我看到他喝了就走。”这话太让我寒心了,我端起水杯就喝,爸爸很想来夺过水杯,手动了一下最终还是缩回去了。
“好,一个人就是要敢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”妈妈说完就出去了,留给父亲的是难堪,留给我的是一个现在都想不明白的问题。
她的话是在否定呢?还是在肯定?
父母劳动一月的报酬,每人扣掉伙食费只有几元钱。
大食堂的饭以山里的粗粮为主,玉米、红苕和土豆出什么吃什么。山上的水酸性重,害得人天天特别想吃油晕。一个月食堂供应每人三两肉,一般都是炒成回锅肉片,往往是肉还在切,外面就排起了长队。
菜以白菜和青菜为主,根本没有油气。在疏菜青黄不接时,自给自足的山上生活,就以盐菜为主,吃了有种想吐的感觉。干部的小食堂当然应有尽有,没有必要去改善大食堂的供应。
一次,学校组织野外拉练,我能带的当然只有粗粮,而班上其它同学却是五花八门,多得可以吃上好几天。我看到他们围住米老师,不断拿出自己带的东西,请老师品尝。我什么都没有,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凑热闹,心里很怕老师叫我过去品尝,这肯定比杀了我还难受。
我偷偷地一个人走了。
我知道所有的热闹、高兴和幸福都是他们的。生活只属于他们,留给我的只有一份压得我几乎窒息的孤独。
后来我就走迷了,一个人就在荒坡上乱转。
米老师找到我时,已经急出了满头大汗。“你为什么不和同学们在一起?”她的责备脱口而出,我无言以对。“我不排除有人歧视你,但班上的同学没有!他们都说是你不和他们玩。”
其实生活的境况早就注定了我和他们不同,也许我真的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
“米老师,我总觉得一个人呆,比大家在一起玩好,一个人死了,比活在这里好。”我的话把米老师吓坏了。深入骨子里的压抑,犹如枯骨滚过黄沙的语调,不可能属于我那个年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