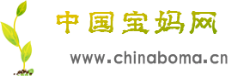以前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,我总是觉得很无聊。全家在一起吃个饭,看看春节联欢晚会,然后出去放鞭炮。那是一种被动的状态,感觉做这些事都是被逼的,但是又弄不明白是被谁逼的。爸爸会冷冷地对我说:“你要是不想去可以不去。”可是每一次我还都乖乖地跟着去吃饭,去看联欢会,去放鞭炮。今年却不一样了,美国这边漫天的玫瑰花,让人想到的是情人节,而非中国的春节。
为了提神,我每次去上SAT家教之前都要在旁边的星巴克买咖啡。我对咖啡的抵抗力特别差,一喝完就极其兴奋,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周三周四因为连着上课,喝了两天咖啡,晚上就没睡着过,周五的时候晕晕乎乎地起床,一翻日历发现竟然要过年了。
妹妹在外头化妆,收音机开得震天响。我咽下一口口水,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从咽喉中直冲上头顶。是苦涩?是委屈?是想家了?我也不知道。我用手撑着晕晕乎乎的脑袋,刚想要哭,克里斯汀却来敲门了。
“咱们得走了。”她说。
我苦笑。我竟连哭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于是我去了学校。可是这种感觉一直没有消失,相反地,它越来越浓重,越来越强烈,直到占据了我整个脑袋。我走下车,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学校的小平房走去。我忽然想到爸爸妈妈,他们在放鞭炮吗?
我直奔Stock太太的教室,她是我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。一走进她的教室我就忍不住了。
“你怎么了?”她抬起头来问。
“今天,今天是中国的春节。”我咬着嘴唇,小声地说。我的手指用力地抠着桌子的边缘。“哦,那就像所有人的生日一样啊!”她站了起来,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,“哈哈,春节快乐!”
我一眨眼睛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“我想家了。”我轻轻地说。我真不想承认,我真不想。
“天啊,Gogo!”她一下子把我拥入怀中。我全身都在抽搐,我把嘴唇咬得很紧很紧。“我想我的朋友,我想……我想北京……”我颤抖地说。
她没有说话,只是紧紧地抱着我。温暖的液体流进了我的衣领里。
“我想过春节……”我说。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承认,我从没想过。
“天啊,Gogo。我理解,我理解。”她也哭得泣不成声,“我能做些什么……让你不这么想家吗?”
我“扑哧”一下笑了出来: “您已经让我感觉很好了。”
我很少想家。我很少承认我想家。这是独生子女最好的地方。我们习惯了孤独,所以在哪里都没什么关系。我每天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雪里等车的时候没想过家;我在小小的基督教学校里过得非常不开心的时候也没想过家,可是在春节这天,就在年三十这天,我的眼泪就不断地流下来,一整节课我都无法控制自己,不停地流眼泪,不停地用沙哑的嗓音发言,不停地被这种强烈的思乡感冲击着。我想家,我想北京,我想放鞭炮,我想吃年夜饭。没有理由,并非被逼,我就是想,强烈地想。
第二天,我照常去了Central Academy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数学竞赛。我讨厌数学,后来我分析之所以去的原因是我对那群数学呆子充满了好奇。很多人有乱糟糟的头发,厚厚的眼镜,但是最后获奖的几乎全是中国人。我站在最后一排,是唯一一个没上去领奖的亚洲人。太 了。我对自己说。然后我笑了,因为我实在不喜欢数学。
Central击败了Iowa city的一所大中学,拿到了第一名。即使是有很多个人没有晋级州联赛,所有的组都晋级了。虽然我不喜欢数学,可还是觉得有些丢人。下了巴士拔腿就想跑,马卡蒂老师一把把我拖过去:“嘿!Gogo,咱们赢了,每个人都得去摸摸奖牌!”于是我很 地跑过去,用指尖碰了碰那奖牌,溜走了。
这就是我,一个人在异乡的春节。
2010年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