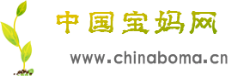我走进文学课的教室,发现教室的右半边挤满了唧唧喳喳的高二学生,只有一张大桌子旁,玛莉亚一个人坐着,盘着手臂,黑色的卷发从眼睛前滑下来,看不见她的脸。
“Hi。”我在她身边坐下来,友好地说。
她微微抬起头,慢慢地把挡在脸前的头发拨开: “Hi。”
她说得很慢,有一丝犹豫。
一开始我以为她有墨西哥血统,因为她小麦色的皮肤,黑色的卷发还有那双美丽、深沉、又有着一丝不屑的黑色眼睛。那双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,忽然变得柔和起来。后来我才感觉到我的幸运。这种柔和,几乎是我们学校那些白人学生从未看见过的。玛莉亚走在走廊里的时候,总是高昂着头,卷发从一边脸上垂下来,只能看见她的另一只眼睛。而那只眼睛里满是不屑与讥讽。
因为那柔和的一瞥,我突然喜欢上了玛莉亚。
玛莉亚从来不参加学校的活动。她转到这所学校两年了,基本上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。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就抱着书,坐到长长的餐桌的一角,眼睛藏在头发下,慢慢地喝柠檬汁。杰西卡曾非常友好地走过去说:“玛莉亚,你应该跟我们坐到一起来!”
玛莉亚头也没有抬,只是摇头。
“可是……”
“不用了,谢谢。”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缓缓地、坚定地说。
杰西卡还想说点什么,但是玛莉亚一下子站起身来走开了。
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尝试去让玛莉亚坐到她们旁边了。不过玛莉亚始终仰着她美丽的脑袋,她不在乎。
春游,秋游,舞会,音乐会,玛莉亚从来不会去。老师们以为她家里穷,给她买了票,她只是低着头,缓缓地但是坚定地说:“不用了,谢谢。”
然后她大步地走开,高昂着头,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讥讽。
有一天,在美术课学生贴作品的墙上,我突然看见了“性手枪”乐队的主唱——那是一张不错的素描,画上是一张扭曲的年轻男性的脸,因为吸毒过多而面颊深陷,青紫色的嘴唇嘲讽地向上扬着,紧紧拧在一起的眉毛下有一双深陷的、迷人的眼睛,眼睛里是绝望、死亡、痛苦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屑。
我盯着这画看,我盯着那双眼睛看,我看见了玛莉亚。
与别的画不同,画上没有签名。
吃饭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三明治和书挪到桌子的角落里,坐在了玛莉亚的对面。
“Hi!”我说,“画儿画得不错嘛。”
她突然抬起头来,缓缓地露出一个微笑。
“你……知道我画的是什么?”
“我必然知道啊!谁能不知道啊!”我激动起来,“天,这是美国,谁不知道‘性手枪’?”
她轻蔑地往桌子那边扫了一眼:“她们就不知道。”
我叹了口气:“她们……她们太虔诚了,她们是不会听朋克的,顶多也就听听基督教音乐。”
她眼中忽然放出了光彩!
“你真的这样觉得?”
“必然啊!”我说,“莎拉天天在车里听乡村音乐还有关于耶稣的歌——谁受得了!”
她看着我,身体向前倾:“那么,你最喜欢哪首歌?”
“New York。”我飞快地说,“你呢?”
“我也是!”她激动地点了点头,“还有Anarchy in UK!”
我伸出手来:“咱们实在应该握握手!”
她也伸出手来,我感觉到桌子那边所有人都停止了说话。
“Gogo! 玛莉亚,你们俩在聊什么?”有人问。
“性手枪。”我说。
她们互相看看。
“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?”我不可置信地说,“史上最伟大的乐队之一!”
“没……”杰西卡说,“不过听起来不是个好名字。”
玛莉亚挑挑眉毛。
我也想学着她的样子挑挑眉毛,不过失败了。
她笑了起来。
“你是墨西哥血统吗?”我问。
她摇摇头:“我是黑白混血。”
“噢!看不出来呢。”
她点点自己的鼻子:“我的鼻子啊,一看就不是白人的鼻子。”
我笑了,她也笑了。
于是,自从那天起,在走廊里玛莉亚再看见我时,她会对我挑挑眉毛,然后转转眼珠,似乎我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。
秋游时,我们住在野外的木屋里,玛莉亚没有去,没有人觉得奇怪。
“我们得想个办法帮帮玛莉亚,”罗杰斯小姐(我们的数学老师)说,“她从来不参加活动——这次我给她家里打了不少电话,但是她就是不来。”
“我觉得她就是自作自受。”罗瑞激动地说,“我早就不想理她了!你知道她叫我什么吗?你知道她竟然叫我什么吗?”
“罗瑞,”我说,“她都不跟你说话啊……”
“在美国政府课上!她说我种族歧视!”罗瑞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所有人都安静了。“种族歧视”这个词是非常可怕的词,没有人会随便说。
“她的确觉得我们种族歧视,”艾米丽叹了口气,“但是实际上没人那样想。”
“我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,”罗瑞伸出手来,“数数看:第一,不跟我们说话;第二,不参加任何活动;第三,叫我们种族歧视——我看她才是种族歧视,歧视白人!”
“罗瑞,别激动。”罗杰斯小姐说,“我搞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想。我们哪里做错了?我问过她很多遍她从来就没有回答过。”
“她说,‘你们不明白’,”杰西卡说,“我希望她能够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,她只是这样回答。”
“上次我说了句奥巴马怎么怎么着的,她就说我是种族歧视!”罗瑞说,“我看我们谁都不必要理她!因为她才是种族歧视呢!”
我没有说话。因为我也觉得玛莉亚这样做的确有些过分。我们班的男生是挺傻的,但是女生一直对她很好。
“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多和咱们班人说说话。”我再一次坐到玛莉亚旁边的时候,我说。“他们种族歧视。”她不解地说,“我凭什么要和种族歧视的人说话?”
“玛莉亚!他们根本就不种族歧视!”我说,“我从来就没感觉到过啊!”
“好吧,那让我告诉你,你如果去公立学校,学生绝对不像他们这样没大脑——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全是白人的学校,我就是觉得和公立学校里的孩子相比,他们完全就是种族歧视!”
“你举个例子。”我说。